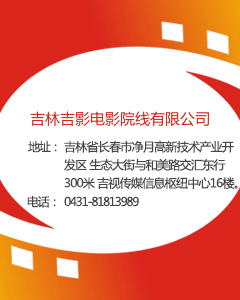中国当下的现实就像是硬币的两面:一面是主旋律现实主义展现的泱泱风范,一面则是日常温情现实主义的“伤痕”抚慰。
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国的现实主义影片出现了一种有意思的现象。一边是充满了政治激情的集体主义呐喊,一边是远离主流社会话语的个人琐碎生活。二者同时被电影市场的主流观众所接受,用票房或口碑达成了自身的“里程碑”意义。
今日在主流和边缘两端摇摆的“现实主义”影片,不仅仅暴露了一部分中国的基本现实,更经由电影叙述和风格的修辞,折射了当代中国人面对新的社会情况、产生的不自觉的矛盾心理。
主旋律的感召力
截至2018年7月,中国电影票房排行榜,第一名为2017年上映的《战狼2》,总票房56.79亿。第二名为2018年上映的《红海行动》,总票房36.47亿。这两部“现象级”影片有着同样的题材和内核:中国军人或曾经的中国军人,在海外危机中拯救同胞以及外国无辜百姓,挫败阴谋,用血与火的搏杀获得力量与人性的肯定。
作为“主旋律现实主义”影片,它们的“现实主义”首先建立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之下。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及在同期的经济危机中独自挺立,给世界经济输送“正能量”,令中国的地位、角色得以突显。与此同时,以工业领先为目标、肯定中国大国地位的社会势力异军突起,成为中国知识界中最有代表性的力量。
随着两艘航空母舰的曝光,对于在“鸦片战争”“日本侵华战争”以及百年近代史里忍受巨大痛苦和屈辱的中国人来说,自立自强的“大国梦想”无疑是最好的疗愈,也是最“正当”的疗愈。
而隐藏在“主旋律”中的“集体主义”意味一以贯之。在20世纪90年代的影片中,人们可以看到“焦裕禄”“孔繁森”这样的模范人物。在上世纪60年代,“雷锋”和“欧阳海”是传颂的对象。虽然经历了“改革开放”,但中国的“主旋律”并没有因此而中断,一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自我牺牲精神依然经久流传。今日的《战狼》系列、《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等影片中,保护集体、牺牲自我的精神依然是最主要的内核。
“主旋律现实主义”影片师法好莱坞商业电影。在意义上,它不再诉诸“以德报怨”“和为贵”的传统道德规则,而是以“以血还血”的政治激情来表明是非立场。在手法上,它不再像过去的主旋律战争影片如《大决战》《大转折》一样,塑造英雄群像,而是高亮某一个体,张扬独特的个人魅力。
经历了美国电影《壮志凌云》《空军一号》,韩国电影《太极旗飘扬》等他国“主旋律现实主义”洗礼之后,中国电影界逐渐认识到搭乘民族集体心理便车、与主流意识形态合作的必要性。同时,这一类影片正是“软实力”的体现,在发达的电影工业制造能力背后,“大国”的影像叙事足以有效宣传自身的政治价值、文化感召力。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是中国古训,但早已不是中国特色。事实上,在这方面做得最出色的是美国,好莱坞早已用它的自恋与自大踩出了一个可复制推广的“软实力示范路段”,中国的商业路数的主旋律电影,大致上是“有样学样”。
默契的实现更多得益于人们的心理需要。以表现朝鲜战争为主要内容的电影《上甘岭》,曾经激励了许许多多的共和国子女,但“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歌声已经随着历史淡漠在时间的深处;而“李小龙”式的功夫奇观,也涂上了英雄迟暮的色彩。生活在集体之中,永远是个人安全感的来源,新的“主旋律现实主义”正是填补了“上甘岭”和“李小龙”之间的想象的空白—那份感情就叫“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主旋律现实主义”的流行,内在的原因正如“朦胧诗”的代表作家舒婷的诗歌《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所表达的那样。在这首发表于1979年并轰动一时的诗歌中,舒婷用“破旧的老水车”“熏黑的矿灯”“干瘪的稻穗”“失修的路基”“淤滩上的驳船”“伤痕累累的乳房”来比喻中国的漫长农业历史和经济的落后,用“飞天的花朵”“古莲的胚芽”“雪白的起跑线”来比喻“改革开放”的中国,并心甘以自身的“血肉之躯”,换取祖国的“富饶”“荣光”和“自由”—同样喷薄的、澎湃的、甚至可以说发自身体本能的感情,每一次都会在时代的转折点、民族主义的高光时刻再度勃发。
日常”获取生存的意义日常温情现实主义影片的脉动从改革开放之初便开始显现。当时电影现实主义的舶来理论与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密切相关,一些第四代和第五代导演的影片,都逐步展现出“巴赞式的”现实主义的倾向:包括在场拍摄、自然光线和声响、远景镜头和长时间拍摄,以及要求观众主动阐释的叙述上的模糊性。
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张艺谋拍摄了准纪录片《秋菊打官司》(1992),他使用了大量非专业演员、广播喇叭和隐藏的摄像机,力图获取一种真实背景下的自然表演。在90年代中后期扬名海内外的第六代导演,像贾樟柯、王小帅、管虎、张元、娄烨、张猛等,均无一例外地采纳了现实主义美学,通过突出那些为主流所压抑的普通人的困境,来展示当代中国的深刻裂痕。
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张猛的《钢的琴》(2010)、贾樟柯的《山河故人》(2015)、管虎的《老炮儿》(2015)依然保持了现实主义的基调。这些作品所表现的日常温情现实主义,和主旋律现实主义的关注点正好相反。如果说后者是在一个庞大的集体层面上进行宏大叙事,高歌改革与现代化的“进步”与“成就”,那么前者则聚焦于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失败者、“零余者”“无地自容”者。
一群钢厂的下岗工人照着一本制作钢琴的俄国文献,正如片名“钢的琴”所言—打造出了一架真的钢琴。下岗、烟囱被拆、生锈的车间、俄罗斯老歌、在贫穷和婚姻告终面前不卑不亢的父亲,以及来自底层的、穷途末路的智慧,背后是这个阶层的没落,旧的经济制度与旧时代的挽歌。“钢”琴作为中产阶层的抽象象征,是东北下岗工人的一种缺位的想象。他们必须靠征服想象来征服卑微的现实。
《山河故人》采用了“三段式”的手法,用三个不同时代的一家人的境遇,串起对历史和未来的拷问。“钥匙”是最核心的叙事道具,1999年,它被主人公扔向房顶;2014年,它被母亲留给儿子;2025年,它已经是一种纪念和信物。钥匙(Key)也是理解影片、理解关于当代中国的“关键”,就像诗人梁小斌的诗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1980)—在顽强的寻找之中,现代化不断趋近的希望和漫长的等待的沮丧,正在普通人的生活里交替上演。
“六爷”曾经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活得有滋有味,却怎么也无法料到自己已经被新世代抛弃。新的跑车,新的北京,新的“顽主”,新的规则。《老炮儿》的残酷在于,曾经存在于王朔、崔健等人身上的、像“红旗下的蛋”“我是流氓我怕谁”的那种睥睨一切的“主人翁”魄力,已经被消费主义的大浪挤压成了泡沫。最后昆明湖那场“战斗”,则充满了“拔剑四顾心茫然”的不合时宜与悲壮。
日常温情现实主义的题材源自矛盾的个人、无奈的现实、暧昧的回忆。每一个普通人都不得不在反讽的、支离破碎的生活里,艰苦地跋涉。“火红的年代”已经永远逝去,民族的伟大复兴尚未到来,和那些挺立潮头、笑傲江湖的弄潮儿不同,普通人只有“日常”,并只能通过“日常”获取生存的意义。
影片也常常通过创作者的“温情”来对“日常”进行抚慰。如《钢的琴》中,陈桂林在桌上画出黑白琴键,教女儿弹琴;如《老炮儿》中在北京闹市出现的鸵鸟,最后总会逃离城市,获得片刻“自由”。这一类影片之所以在当下获取良好的口碑,与其自身对普通人生活的真实反映以及对困苦的安慰是分不开的。
中国当下的现实就像是硬币的两面:一面是主旋律现实主义展现的泱泱风范,一面则是日常温情现实主义的“伤痕”抚慰。中国社会发展不均衡的现实,是“现实主义”影片呈现撕裂感最主要原因。
颇值得玩味的是,生活在一二线城市的“白领”观众,多看重日常温情现实主义的批判性;而“小镇青年”们更喜欢主旋律现实主义带来的满足感。从票房数据也可以略知一二,像《战狼2》的56亿票房,不可能仅仅靠少数票仓城市的观影人群拉动,而是靠极大地下沉到中国的毛细血管——县城去完成。
这种情况的出现,其中固然有物质的因素:县城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熟人社会”的稳定感,虽然收入较低,但消费也并不高昂,医疗、教育资源(虽然算不上最好)都较为容易获取,人们对“过日子”也充满了耐心。大城市则“居大不易”,即使可以“躲进小楼”,实现个人的“自由”,但生活的基本要素依然极度稀缺,那种“不安全感”很难得到克服。
从文化层面上来看:城市里较好的公共文化资源和发达的教育资源,培养出了极具现代意识的“公民”。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权利”学说来考量周围的一切,并更加有意识地希望通过文艺作品,来表达个人的生活史与内心世界。这些过于“务虚”的需求在县城就很难实现。
日常温情现实主义影片注重用个人历史来表达价值观念,而个人历史往往又渗透了中国当代的现代化改革、城市转型、全球化贸易与大众文化爆发等事件,这些兼具回忆和安慰功能的故事,对于一二线城市饱受“焦虑”折磨的观众具有更强大的向心力。而建立在一个共同历史基础上的主旋律现实主义,更容易挤出“小镇青年”的肾上腺素。
这也是为何第四代、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都不约而同地利用“日常温情现实主义”来进行创作—历史和现实是交织在一起的搅拌机,生在其中的人们根本无法从中剔除任何一种因素。对于第四代和第五代来说,沉重的历史包袱是他们终身无法卸下的压力:政治理想主义和激情不仅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启蒙资源,也是他们“弑父”的最终武器。
对于第六代来说,他们有意忘却“旧”的历史的伤痕,用新的“历史”发泄自己的青春怒火。当时间来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昔日的“小武”都已“长大成人”,他们苦苦盼望的“成人礼”已经消失在地平线之上,最叛逆的青年成为“一声叹息”的“老炮儿”。
无论是谢晋的《芙蓉镇》、陈凯歌的《黄土地》、张艺谋的《红高粱》,还是管虎的《头发乱了》、娄烨的《颐和园》、贾樟柯的《站台》,这些现实主义影片虽然回应了不同的历史和现实,但共同的功能就是—拂去荒诞岁月施加的泪水,包扎人性角逐留下的伤痕。
归根结底,电影既是现代技术,却也拥有魅惑、治愈以及在自然与文化间营造精神感应的力量。早在193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电影就已经开始有效处理一个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发生的冲突和异化。今日混杂了大量商业色彩的现实主义影片,包括主旋律现实主义,也包括日常温情现实主义,很多情况下都囿于情节剧的套路、虚拟的戏仿,并在价值观上明哲保身,但其中的“慰藉”依然显而易见:在深刻变异的、多元的社会环境下,中国人饱含着期待的失落,而又充满着自信。(荣智慧)
- 上一篇:第十四届长春电影节 霍建起任评委会主席
- 下一篇:电影的平民时代来临
当代中国电影:主旋律现实主义与日常温情现实主义的交相辉映
来源: 发布时间:2018年08月03日